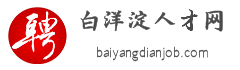第三代打工者生存现状:活在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

第三代打工者在守望城市。他们已经完全脱离农民身份,没有故乡可回,成为一代“新工人”。
法治周末记者 宋学鹏
吕途大学毕业已近20年,但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所以她去苏州的一家工厂面试时,谎称自己28岁。她混过去了,被录用了。
“苏州的那家工厂每天有无数的打工者离开,同时又有好几百人进厂。那么多人都在工厂门口等着,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那感觉就像在等着进屠宰场。等终于叫到你名字的时候,你要跟着站成一排一排的,等着分厂,这时你就会觉得特别丢人。但是你又很渴望被叫到你的名字、站在那儿去丢人。”吕途回忆起她为了做社会调查去工厂打工时的经历,“一些感觉我无法通过对工友的访谈得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自己去。”
从2010年5月到2011年6月,吕途和她的同事去苏州、深圳、重庆、北京、武汉等地的打工群体中进行调查和采访,研究这个群体的现状和动态。这个打工群体,她把他们命名为“新工人”,他们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却在农村的打工者。一直以来他们都被称作“农民工”——一些打工者接受这个称呼并且也这样称呼自己;同时也有打工者,尤其年轻人对这个称呼感到反感,觉得这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称呼。
2012年2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称,(2011年)全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吕途和她的同事们调查、描述的正是这个庞大的群体——一个在经济崛起的制造大国和在城镇化浪潮下诞生的“新工人”们,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在厂房里,没有人会叫你的名字。生产线上的线长会拎着你的衣服领子,把你从一个岗位提溜到另一个岗位。从来就不会问你叫什么,你也从来不知道他叫什么。这是一个让你没有名字的世界,在这里,当有人真的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卑,有一种千万别提到我的名字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吕途停顿了一下,强调了一下最后一句,描述完她体验到的打工者的世界。
到他们中间去:一个中国新工人村庄
吕途在北京的皮村有一间宿舍,这是她工作落脚的地方。
皮村是北京朝阳区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的一个村庄,大约有4路公交车经过这个村庄。在皮村的公交车车站总会看到三三两两的打工者拉着皮箱在等公交车,街道上的垃圾和不规整的店铺比公交站牌更显眼。而头顶上不时飞过身形庞大、轰鸣的飞机表明这里离首都机场很近。也因位于机场航道下方,皮村不被允许建高层建筑。在低矮的皮村,和吕途走在曲曲折折巷子里,才体会到这个未被拆迁的村庄,在等待未来命运时的杂乱和无序。占用到街道的出租房,是为了满足外来的打工者,更是为了下一次拆迁时换取更多的补偿。
2009年,因与之近邻的曹各庄被纳入新的建设规划之内,聚集在那里的外地打工者被迫搬到了皮村。这让皮村的外来人口大涨。现在皮村的本地人口有1000多人,外来人口却有1万多人。和中国很多的村庄一样,皮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村庄,而是“未来的城市”。
根据吕途所工作的机构——北京工友之家在2011年7月的初步统计,皮村大概有大大小小的工厂205家,工厂雇用的工人从4人到200多人不等,平均每个工厂的工人有大约17人。“这样统计下来大概有3485人在皮村的工厂上班。当然居住在皮村的打工者也有很多是每天去附近和城里上班的。村里有两所为打工子女开办的民办小学,有1000多名孩子在这两所学校学习。”吕途介绍说。
吕途所服务的机构——北京工友之家就在皮村,和工友之家的接触改变了吕途。吕途1990年代初在北京一所大学毕业后并留校任教,1997年她开始去荷兰读了社会学的博士,其间和其后一直从事国外扶贫发展援助项目的社会学调研。
2003年,吕途在参与一个亚洲社会研究项目中开始了针对打工者群体的调研,北京工友之家成为她调研的对象。但她的调研并不为工友们所认可。“他们对我也不是很热情,他们认为我的调查研究没有什么作用。正因为他们对我的研究虽然也合作但是持批判的态度,让我有一个反思,就是你的研究有用吗?”吕途做了多年的社会学调研在这时遇到了挑战。
“其实,你看到的、你想的都是你想看到的、你想想的。这是当时一位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对我讲的话,对我触动特别大。原来我根本就没有能力认识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自己。”这帮助吕途完成了一个研究者的转型,“我发现我的研究没有用,我的研究只服务于我的研究,不会服务他们。你要想真正做研究,真正为你所声称的那个群体服务的话,你就得生活在他们之中。”这才有了吕途到打工者群体中去工作和生活的一幕幕。
在皮村工友之家的大院里,有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新工人影院、新工人剧场,这个普通的大院几乎包含了皮村所有为打工者服务的文化场所。在大门右边的一长排红瓦房就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博物馆正在为荷兰艺术家马泰关于“中国工人1000个梦专题展”做着一些准备。
掀开厚厚的门帘进去,入目的一个长廊一直通到房子的尽头,在规格相等的几间屋子里,陈列着来自全国各地打工者的照片、信件、暂住证、就业证、工资单、欠条、劳动合同、生活用品、工作服、劳动工具等。这是一个在北方大院普通房间里的博物馆,堪称简陋,但陈列和展览足够真诚。对于这些,博物馆的创建者孙恒说了一句话:“在主流的历史中,我们听不到劳动者的声音。历史放在这里并不是为了陈列,而是为了促进我们思考和进步。”
采访当天的下午,吕途要去给在皮村的打工子女学校——同心实验学校的学生上一堂课。这个去年夏天经历关停风波的打工子女学校现在继续维持办学。在四年级的教室里,荷兰艺术家马泰正在为孩子们展示荷兰解决移民子女入学受教育问题的一些历史和现实图片。教室有些简陋,孩子们好动,教室里时而安静,时而嘈杂,但整体气氛活跃,吕途担任翻译有时不得不大声地喊着对孩子们讲话。
课上到一半时转到六年级,六年级的学生安静很多。比起四年级的孩子,六年级的课堂更有秩序。在马泰展示的一个年满18岁的非洲籍学生面临被遣返的境地的照片时,马泰让学生回答该不该让他离开荷兰回到他自己的国家时,这个触及这些孩子处境的问题显然刺激了他们。在最初的沉默之后是热烈的讨论,应该的与不应该的、合法的与不合法的,不管是沉默还是回答,每个人内心都有着自己的答案。六年级,意味着他们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去哪里继续上学。
课堂结束时,吕途问这些学生:“明年谁会离开自己在北京打工的父母回到家乡上学?”大约有一半的学生举手;“谁能确定知道自己能在北京继续读初中的?”只有三四个学生举手。而剩下的都不知道自己明年到底在哪里、做什么。
“土扶可城墙 积德为厚地”,在教室斑驳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用毛笔写的不甚工整的字,装饰着这个简陋的空间。与四年级的活泼的孩子相比,六年级的学生们有那么一丝不易觉察的沉默。
根据2009年北京工友之家的《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在北京皮村居住的打工者平均每人的居住面积是4.6平米。很多家庭因为住房和经济的原因,而不得不选择把孩子留在老家。
在皮村听到了一首北京工友之家新工人艺术团为生活在北京城乡接合部打工者聚居区的工友创作的歌曲《这矮矮的村庄是我们在这城市的家》(词曲:许多)。在掺杂着各地方言的音乐中,他们在诉说着打工的漂泊生活,让人眼前浮现出“新工人”的皮村:
村子里那一排排一间间十来平米的小屋中
大伙用不同的方言会说些相同的话题
大伙早晨挤上公交车,挤进这城市的文明
然后就去勇敢面对生活的艰辛
哎!
……
村里有所简朴的打工子弟学校
孩子们在这能学习,开心地玩着游戏
村子旁边那个工地上,戴着安全帽的老乡们
在辛勤地为别人盖着漂亮的房子
哎!
……
我们带着双手和行囊远走四方
我们努力生活就不会失去方向
那破旧的录音机里放着西北的秦腔
他铿锵有力地唱着生命的力量
那破旧的录音机里放着西北的秦腔
他铿锵有力地唱着生命的力量
力量——
我劳动 故我在:答案就在我们的劳动里
吕途将她这几年的调查报告写成一本书《新工人——家在哪里?》,今年1月这本书以《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书名正式出版。在书里,她调查描述了打工者们在城市的生存状态,调查了他们回不去的故乡,描述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在城乡之间的迷失。
要想在吕途的书里找一个答案似乎很难,问题是多于答案的。工友杨猛说:“当我读了第一遍的时候,我感到很痛苦,因为我不知道作者是否有意在让我们自己去领会我们工作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找不到答案。”
杨猛,1986年出生,四川宜宾人。他说话温和、诚恳,脸面上带着笑容,有一种同龄人身上所少有的沉稳。杨猛是第二代打工者,他最初的身份是留守儿童。他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带着他的弟弟去浙江打工。“在我留守家乡的过程中,我分别在姑妈家、奶奶家、外婆家住过,我就是一个流动在家乡的留守儿童。”杨猛用他缓慢而温和的语调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2007年,杨猛开始他的打工生涯,他的第一份工作,就在他家乡相邻的镇上。“因为家乡的经济条件特别差,不能满足我的发展。所以,2008年我开始外出打工。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我去过深圳,苏州、西安和北京。”
2009年,杨猛成为北京工友之家同心创业培训中心的学员,后来开始参与北京工友之家的工作。现在他在这里负责网站的编辑工作和一些培训工作。“他给工友讲的是法律课,主要讲工人的权益保护方面的一些知识,大部分都是他从自己的经验里总结加上自学得出来的。”吕途介绍道。她在杨猛身上看到了“新工人”萌芽的东西。
杨猛对记者说,他很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因为他已经回不到农民身份里,在农村他已经不能养活自己,他只能在工人的劳动里生存下去。“我们用我们的劳动报酬支持我们边远家乡亲人的生存。我们的存在决定着城市和家乡的发展。”当然,杨猛也意识到这里面的变化:“20年前,我父亲一个人外出打工可以养活一家人,我现在一个人外出打工却很难养活我自己。我们的父辈可以十几年,二十几年在低劣的条件下工作下去,而没有任何的怨言。但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了。我们的意识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不断地进步。我们的参照物是我们的前一份工作。我们在不断地换工作,也在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们不断换工作,不断追求好的工作状况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整个意识在不断提升的过程。”
全国总工会做的《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每年变换工作0.26次(也就是说平均3年就要换一个工作),传统农民工为0.09次(也就是说平均11年换一次工作)。
“在和工友的交流中我发现,工友的工作稳定性差别很大,有的工友一年之内也许就换好几份工作,而有的工友可能10年都在一个厂里工作,但是总的趋势很明显,打工者的工作是很不稳定的。”吕途说。她调查总结了新生代工人换工作的几个原因:因企业条件和工作性质所迫被动离开、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主动离开、道德的选择(觉得所从事的工作太没有良心了,就选择离开)。
不断地变换工作成为中国新工人抗争、希冀改善条件与争取发展自己的一种方式。《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在对待工人伦理缺失的情况下,国家体制、工厂主、中产阶层或者相对的富人阶层都没有从工人作为人所应有的基本需求来界定工人的生存状况。我们在讲新工人的时候,应该也对我们整个社会提出要求。”
吕途在调查中发现这些打工者很难有归属感:“那狭小简陋的临时住所也不是他们的家。工友即使在一间工厂一座城市工作了十几年,还是无法安顿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还是在疑惑自己的家在哪里。谁会对这样的生活满意呢?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生活应该至少包括下面三个内容:就业权、居住权和子女受教育权。”
“我在想,20年后,我们新工人群体的下一代是否还能够养活他们自己。我想,他们应该可以养活自己的,因为我们的意识在觉醒。”杨猛说,“我们通过自我意识的提高,然后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有一个重新的定义和认识,然后体现在我们以后的行动中,这才是真正的答案。答案就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不断地去接触劳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吕途希望正在于此。她坦然而热切地说,“中国社会在过去30年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追求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那么就必须重视这2.5亿打工群体的诉求。过去30年,是打工群体在人数上的形成过程,那么今后的几十年是这个群体谋求社会进步和群体地位的过程,而代表这个群体诉求和发展方向的词也许就是‘新工人’。”
在告别起身时,看见吕途宿舍靠近门口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切•格瓦拉的画像。
“我喜欢格瓦拉。”吕途补充道。
“那读马克思的书吗?”
“读,我很喜欢马克思的一些论述。有时晚上苦恼时读马克思的书,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道德、情感和力量。”